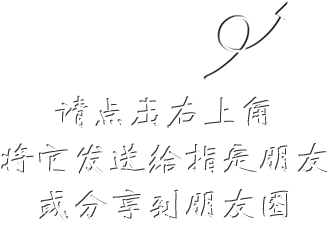颈椎手术并发症的研究进展(二)


本文原载于《中华骨科杂志》2016年第17期
二、前路手术并发症
(六)霍纳综合征
颈部交感神经节的损伤可能导致损伤同侧的霍纳综合征(表现为瞳孔缩小、眼睑下垂、面部无汗),文献报道发生率为0.1%~1.1%[8,11]。颈交感干走行于颈血管鞘和颈长肌之间,任何对于颈长肌外侧的牵拉以及外侧的过度解剖均有可能造成其损伤。霍纳综合征通常是一过性的损伤,目前认为颈长肌的骨膜下剥离可以避免其损伤[62]。
(七)植骨不融合与假关节形成
颈前路术后假关节形成的发生率为0~50%[2]。主要的危险因素在于吸烟、骨质疏松、多节段融合、手术技术、生长抑制剂的应用等。人工骨、骨形态发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BMP)等骨移植替代物的应用通常可以改善手术节段的融合率[63]。然而,前路手术中BMP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为0.66%~20.1%,会增加前路颈部肿胀、吞咽困难和呼吸困难等并发症。关于BMP的并发症尚无明确的定义,一些专家认为BMP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在于BMP的溢出以及应用剂量过大[64]。BMP-2是未经过临床试验证实的药物,并且被FDA进行了安全警告。由于其可能发生严重的潜在并发症,术者选用时必须仔细衡量其利弊。
(八)内置物相关并发症
手术区域植骨移位的发生率在2%以下。目前,钛板、螺钉以及融合器的应用能够限制上、下椎体对植骨的应力作用,可以防止植骨的退出。
内固定物的机械疲劳或材料瑕疵可能会导致内固定失败,但是内固定物的力学失败非常少见[65]。颈椎前路手术后螺钉退出的发生率大约在0.1%以下[4],对退出螺钉进行力学和材料学检查,也未发现其存在材料学方面的缺陷。螺钉退出与螺钉-椎体接触面的愈合有关,过早的颈部活动会增加螺钉-椎体界面的应力。如术中选用不合理的融合器以及螺钉置入位置不良则更有可能造成屈曲位时螺钉应力集中而导致螺钉退出的发生[66]。
(九)人工椎间盘相关并发症
颈椎人工椎间盘的临床价值目前还存在异议,但是目前中、长期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提示人工椎间盘能够在同样改善患者神经功能的同时降低邻近节段退变的发生[67]。
异位骨化是人工椎间盘置换术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可能与磨钻使用后产生的骨颗粒在手术区域周围聚集有关[62]。术后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可能通过抑制环氧化酶从而阻止前列腺素的合成,进而阻止间质细胞向成骨细胞的分化[66]。
假体的移位、下沉与假体大小的选择有关,选择合适大小的假体可以避免其移位[68]。
三、颈椎后路手术并发症
(一)轴性痛
轴性痛的概念在1996年首次在文献中被提出,其定义为沿颈项部至肩背部或肩部的疼痛[25]。项背部的疼痛最为常见,严重的轴性痛会在坐位和站立位加重,仰卧位减轻。双上肢的位置也与轴性痛有关,通常在高举时缓解,而在双手放下时加重[53]。大多数患者在术后早期即可出现轴性痛,然后逐渐减弱[69,70]。当然,严重的轴性痛可能长期存在,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71]。
轴性痛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但临床实践中发现颈后部肌肉萎缩和损伤是轴性痛最明显的病理改变。有学者认为术中颈部肌肉损伤越多,术后轴性痛就越明显。手术后并发慢性轴性痛也可能是颈部伸屈肌肉力量不平衡导致的失代偿所致[72]。Yoshida等[73]研究发现脊髓后角细胞损伤与轴性痛有关。单开门手术中棘突偏离正常解剖位置使颈后部肌肉无法重新与棘突接触,这可能与单开门手术后轴性痛发生率高有关[74]。另外,C2、C7附丽肌肉保留与否也是轴性痛的相关因素[75]。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了C2半棘肌的保留与修复可以预防轴性痛的发生[75,76]。C7棘突作为斜方肌和项韧带的起点,Hosono等[77]发现保留C7后部结构比C7周围肌肉的保留对预防轴性痛更有作用。有文献指出跨节段的椎板切除以及选择性椎管成形可以更进一步减少颈部结构的损伤,从而降低轴性痛的发生。
对于轴性痛的治疗目前多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案。Edwards等[8]应用颈托制动以及颈肩部肌肉力量训练达到了缓解疼痛的目的。Kawaguchi等[78]在颈后路手术中减少术中植骨量的同时缩短术后颈托应用时间,并且加强患者术后的早期锻炼,在减少轴性痛发生率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椎管内血肿
颈椎后路手术后CT检查发现硬膜外血肿的发生率为33%~100%。大部分血肿并无临床症状,出现临床症状的硬膜外血肿发生率在1%左右[79]。但是椎管内血肿一旦出现临床症状非常致命,临床症状可为迅速扩散的四肢麻木和突发的呼吸功能障碍等。及时诊断和再次手术探查非常关键[80]。
与颈椎前路手术后血肿不同,颈椎后路术后椎管内血肿可能与年龄、凝血功能障碍、Rh+血、术前非甾体抗炎类药物长期应用、多节段椎板切除、术中出血量多有密切关系[81]。术前对患者进行上述椎管内血肿危险因素的评估是预防此并发症的重要措施。
(三)吞咽困难与呼吸困难
呼吸困难和吞咽困难常见于颈椎前路手术并发颈部或咽部血肿的患者,而在颈椎后路手术患者中少见。上颈椎手术中枕颈部的屈曲位固定融合是不常见的、能够导致患者吞咽及呼吸困难的原因[82,83]。严重的呼吸困难可以在术后麻醉拔管后即刻出现呼吸窘迫症状,从而不得不再次插管。轻、中度的呼吸困难和吞咽困难虽无生命危险,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患者的生存质量,诸如睡眠中的被迫仰卧体位,进食软食等。其原因可能与咽部空间的减少和活动度的降低有关[84]。
Matsunaga报告C0-C2角对于维持患者正常口咽部面积的重要性。Suk等[85]则认为McGregor线和枕颈连接角(angle of craniovertebral junction,ACVJ)对于患者正常张口是最重要的测量指标。这些指标的测量不能仅依赖于术前检查,术中测量以及对患者体位的调整对于上颈椎正常曲度的固定融合十分关键。Miyata等[82]研究发现即使术中、术后的C0-C2角相差-10°~-5°,临床也会出现呼吸困难和吞咽困难。
(四)内固定物相关的并发症
颈椎后路手术方式多样,内固定技术也有多种类型。目前临床主要应用的有寰枢椎螺钉、寰枢椎经关节突螺钉、侧块螺钉、颈椎椎弓根螺钉以及微型钛板等。寰椎螺钉退出的发生率为0~4%,枢椎螺钉退出的发生率为0~7%[86]。寰枢椎经关节螺钉有椎动脉损伤及神经损伤的风险,椎动脉损伤的发生率为1.3%~4%[36],神经损伤的发生率为0.2%左右[87]。
椎动脉损伤是螺钉应用中最严重的、也是最常见的并发症。后路手术由于内固定器械以及部位的不同,发生率自上颈椎的4.1%~8.2%到侧块螺钉的0[37]。颈椎后路手术中椎动脉损伤常发生于用磨钻开孔、扩孔和螺钉置入的操作过程中,主要是因为螺钉轨道的不可见性[37]。椎弓根螺钉在下位颈椎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侧块螺钉更大的稳定性,但有更多的椎动脉损伤风险。Kast等[88]的研究显示椎弓根螺钉虽无发生椎动脉损伤病例,但10.6%的螺钉(10枚/94枚)在术后CT检查中发现进入椎动脉孔。
下颈椎的侧块螺钉还有神经根损伤(1.3%)以及侧块骨折的风险[89]。目前的术中CT技术以及计算机导航技术进一步减小了螺钉偏离的问题。2003年,Kotani等[90]报告导航技术辅助下螺钉错位发生率为1.2%。同样,Richter等[91]也报告导航技术辅助下椎弓根螺钉置钉时椎弓根的穿透率为3%,比直视下置钉的穿透率减小了5.6%。
(五)后凸畸形
颈椎后路多节段椎板切除术后并发后凸畸形的发生率为14%~47%。老年患者可能因随访时间短、颈椎的增生退变导致椎体间部分融合而发生后凸畸形的概率较年轻人低。
颈椎后凸畸形是由于椎板切除术后颈椎失去后部结构的支撑而导致颈椎不稳,随着颈部后伸肌群的失代偿从而导致后凸畸形出现。Guigui等[92]报告椎板切除术后后凸畸形的发生率为31%(15/58),而其中高达5%的患者需要通过手术再次稳定颈椎,因此,建议对患者进行详细的术前颈椎稳定性评估,以排除后凸畸形的发生风险。Kaptain等[93]对46例行椎板切除患者进行手术前后的动力位X线检查,结果提示术前颈椎曲度"变直"的患者术后颈椎后凸发生率是正常颈椎曲度患者的2倍。在施行椎板切除的同时对颈椎进行融合手术可能能够阻止后凸畸形的进展[2]。
(六)"再关门"
单纯椎管成形术的"再关门"现象是常见的手术并发症,其发生率约在40%左右。Matsumoto等[94]指出最常并发"再关门"的节段为C5和C6,最少发生"再关门"的节段为C3和C7。Lee等[95]对接受椎管扩大成形术后的患者在术后6个月进行CT检查,发现有10%左右的"再关门"现象,但是神经功能却未受到影响。Wang等[96]重新分类了"再关门"种类,将其分为单节段型、多节段型、完全型、部分型四类,并将椎管前后径为4 mm作为指导临床治疗的分界,当患者椎管前后径<4 mm时,则该节段狭窄与术后的神经功能恢复不良有关,可能需要再次手术治疗。
为减少"再关门"的发生,目前也有很多方法供术者选择,如门轴侧的铆钉固定、开门侧的植骨以及微型钛板支撑,均能够减少该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无论颈椎前路手术亦或颈椎后路手术均能为患者解除脊髓压迫,但在手术过程中术者除了直接面对脊髓神经损伤的风险外,还有很多与规避并发症(感染、牵拉、内固定等)的相关细节值得注意。虽然大多数的颈椎手术相关并发症可以预见,但仍然存在发生机制不明的并发症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略